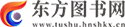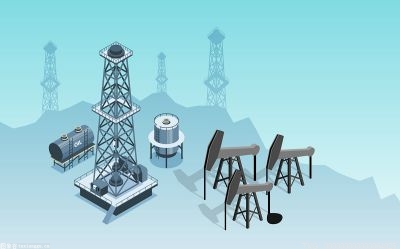(资料图片)
(资料图片)
萱草聊戏 | 阿那亚戏剧节《虫子》
恐怖酸涩 活人偶剧
太过真实往往虚幻,当卓越的演员出现,他其实是个面庞清秀的小伙,但当他装束成一只大虫,女孩们恐怖大叫,他扑向了中间后排的观众,前倾的“虫身”触及那些女孩。
法国人浪漫到骨子里,在一种惊惧、神经质中疯狂渲染,此时的幽默仿佛镇静剂和迷幻药,当他们“车碎了”一个人的身体,各种“零碎儿”散落,这时我们的口中腥咸,五味混乱,方才的一丁点儿“温馨可爱”变作酸涩难耐,调一种古怪的鸡尾酒,让你欲罢不能,又痛苦失声,四个演员中格里高利扮演者又饰演了三个角色,令人惊叹。
面具发挥了无可比拟的象征意味,所谓能剧的变体,他们模仿木偶的步伐,动态,让一切规律简洁象征陌生化,充满诗意,从来只看过木偶模仿人,初见人模仿木偶,简直怀疑他们不是真人,但分明除了面具,都有血有肉,看得见肌肤和汗毛,这样的演技真是一种超越。
格里高利变作的虫子由小偶,中偶,大偶和一些长触须组成“扮演团队”,均由演员驾驭,但演员隐身,而格里高利本人则披着重重的虫子铠甲,像一个角斗士,将虫子的恐怖和这家人的残忍演到极致。
在极简的舞台空间,用长墙板遮蔽,演员隐藏其下,冒出头和身躯即显形,开始表演,这种古老的演绎手法很适合精炼一台戏的舞美和舞台调度,演员们来回穿梭,有时到台前,像儿童们玩的过家家童话剧,七十分钟的卡夫卡《变形记》就演完了。
化妆的精致堪称一流,我坐第一排觉得也无可挑剔,每位扮演格里高利家人的演员都生着一副善良的面孔,却以最惟妙惟肖的“人偶面具”扮演了人性中最丑陋的角色,他们自私地以为格里高利应该一直为他们的享乐而工作,当虫子格里高利绝食以致活活饿死的时候,他们以一趟旅行来忘记这“不愉快”,观众们如梦方醒,掌声雷动,并努力学着不怨恨不讨厌面前的扮演者——格里高利的父亲,母亲和妹妹。